我,曾砍倒一棵树。我见它枝折叶落,我看见雨滴在树桩上凝成泪痕。
砍树的人志得意满,一去不返。一个月后,树桩旁舒展出侧芽;一年后,侧芽变成枝条;三年后,枝条忘情地延展出枝極;十年后,树有了名叫时间的年轮,灭顶的创伤、横遭的劫难都被一一治愈。所以,是时间治愈了被我砍倒的树吗?是,又不是。树稍已华枝春满,而我一点点蹉跎,时光都钝刀,一点点剜下我的皮肉,我的心志.....
时间只是容器,真正治愈的,是我们究竟做了什么。树只在生长,而我只在老去。
时间于树于我,公平如斯。它无温无情的流逝,不具备抚平创伤的能力,却为生命提供了向上生长的机会。每一个在创伤中挣扎起身的人,就像那棵被砍倒的树。若不是在树桩深处藏着未灭的生机,若不是在风雨中拼力汲取养分、抽发新芽,即便给它光阴,也只会在腐朽中归于尘土。古往今来,多少生命困于绝境,并非时间未曾馈赠机会,而是自身早已熄灭了生的火焰。那是屈原遭贬谪、受排挤,纵身旧罗江的那一刻,他找到了精神的永恒,可时间再难为他续写生机;那是李煜沉溺故国之思,徒叹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,天上人间只会让他的悲戚愈发浓重,却换不来自愈的契机。可见,时间的意义,全凭生命自身赋予:你若向阳而生,它便为你滋养枝叶;你若向暗而眠,它便任你归于荒芜。
我想,真正的治愈,是生命在时光里的自我挺立与温塑。
怨斧斤之伤,也未曾沉溺于枝折叶落的痛楚。这份自甘愿和自愈,藏在史铁生的轮椅辙痕里。双腿瘫痪的重创,曾让他在地坛的角落里反复叩问生死,时间没有直接抹去他的痛苦,却给了他与自我对话、与草木相融的空间。同样,苏轼屡遭贬谪,辗转流离,岁月将他从汴京的繁华推向儋州的蛮荒,却未能磨折他对生活的热忱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淡然恰是他=生命里最动人的风骨。他未曾等待时间治愈,而是以豁达为种,以热爱为泉,在岁月里耕耘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时间如水,“愈”在心上。治愈从来不是人与时间的单向等待,而是在岁月流转中主动为生命赋形。时间的价值,从来不在“抹去”的功力,而在“承载”的厚度。是时候了,我们该反思、行动。倘若只是被动静待时间“治愈”,只会在流年里日渐空芜;唯有主动在时光中耕耘,用行动熨平遗憾,用热爱填补创伤,方能让过往的坎坷都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。那些历经失去的人,从不是时间帮他们淡忘了伤痛,而是他们在岁月里学会了与自己重塑。我们终将收拾好行囊,继续奔赴往后的山河。
行文至此,掩卷覃思。少时所读《儒林外史》里范进的脸庞,竟在时光里愈发清晰。
“年年考,月月考,活活考死你这命一条”,科举的枷锁将他因在岁月的泥沼里,半生蹉跎,满心执念。反观那棵被我砍倒的树,它不懂功名,不知执念,只守着一份向阳而生的本能,在时光里自我修复、默默生长。我想,该打破执念了。该主动为生命赋形,方能在岁月长河中,不被时光磨蚀,反而如树一般,在风雨后愈发挺拔,在流年里绽放华枝。
“如月之恒,如日之升。愿时光永赋予我,愿我永可愈我。
时光永赋予我,我永可愈我
时光永赋予我,我永可愈我
温馨提示:
本文最后更新于2026年01月18日,已超过51天没有更新,若内容或图片失效,请留言反馈。
版权属于:
chboy
作品采用:
《
署名-非商业性使用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(CC BY-NC-SA 4.0)
》许可协议授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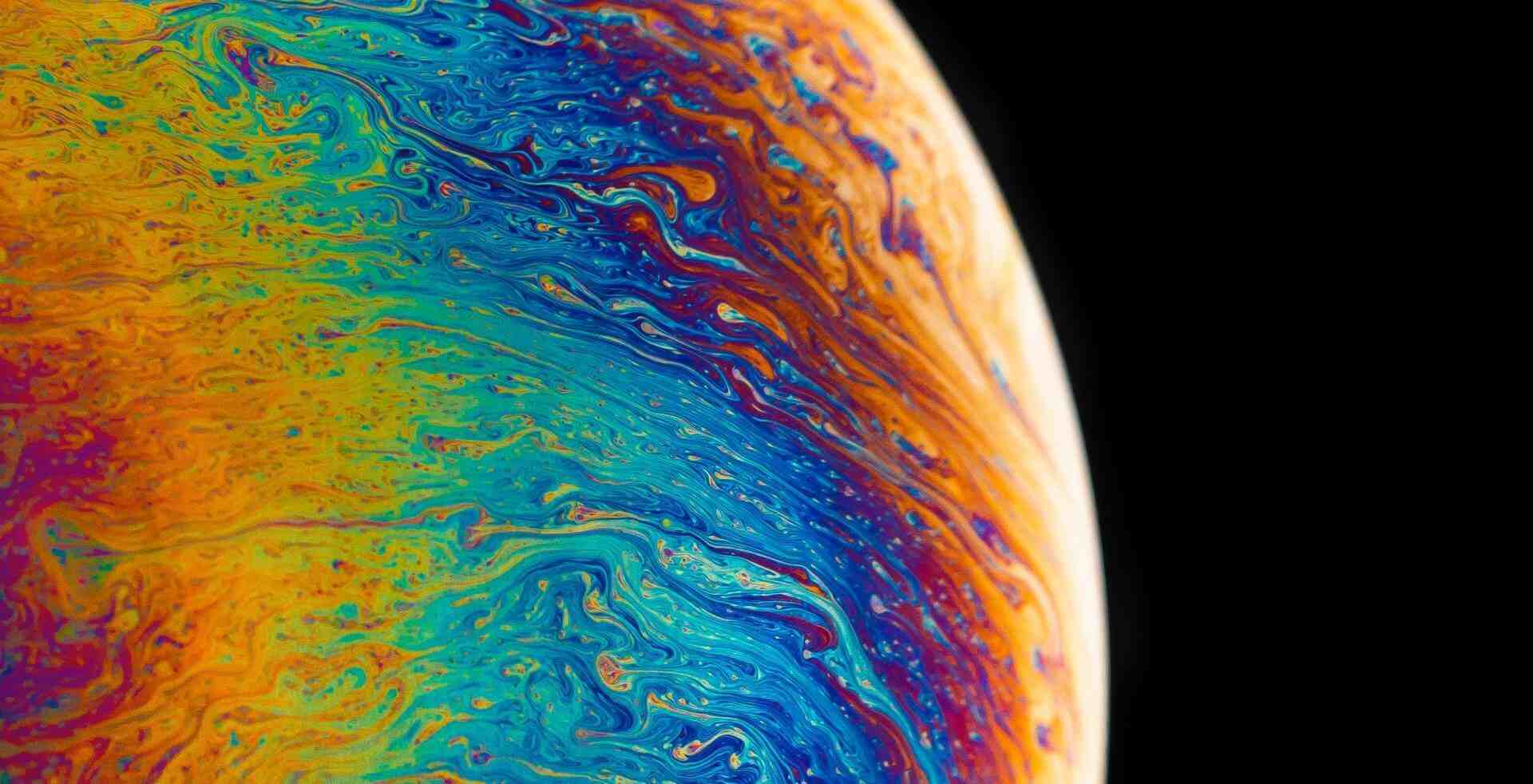
评论 (0)